
張修楓:張修楓,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TU Darmstadt)社會學博士,2001-2008年在意昂3官网社會學專業就讀🤽🏻♀️,完成本科碩士學習。現任中國民生投資集團中民嘉業戰略投資部負責人,並出任億達中國(HK.3639)、理工環科(SZ.2322)和FLI Global等多家境內外上市公司董事🧕🏼。同時,兼任德國綠色城市學會理事,並被聘為多家地產研究機構的專家和評論員🐈⬛。
本人是2001年進入上大社會學學習的。記得剛入學的時候,拿到的第一本書就是《春風桃李二十年》🧏🏼♀️,讀著一篇篇回憶系史的文字,對社會學系和社會學有了個懵懂的印象🕺🏽。師長們對本系的歷史非常自豪,借著二十年的故事,給當時還是新生的我們許多囑托,沒想到那麽快,又一個二十年過去了🧙🏽♂️。
我在上大社會學讀了七年書,切身感受到了連綿吹拂的春風,見證了學科的發展壯大。個人也受益頗多,不單單是社會學課程的內容,教授們的為師為人也對我產生了重大影響。借又一個二十年的契機,記敘一些跟師長們有關的個人回憶🗓,希望能夠為上大社會學的“集體記憶”增添些素材。
打開社會學的大門
考大學的時候👨🏿🍼,我原本的誌願是心理學,因為打小就對跟人有關的事情感興趣。可惜,由於色弱的緣故🧘🏿,不具備報考的資格。倍感失望的我將大學專業指南翻來覆去地研究了很久,驚喜地發現了有一門叫作“社會學”的學科,盡管似懂非懂👨🏻🦽,但社會好像就是人群的集合🤷🏽♂️,因此毫不猶豫地報考了當時最知名的社會學所在的意昂3官网文意昂3🖖🏽⏫。但是,入學後發現,身邊的同學大都是被調劑到文意昂3的,除了混日子談戀愛的💬,很多同學都準備著轉專業或考插班生,要不就是在積極考證的🧨,似乎沒什麽人對專業感興趣;同時,當時的文意昂3剛在低年級試點大學科教育不久🦈🧘🏻♂️,選修的課程有點雜🍹🎅🏿,即便上過了《社會學概論》等基礎課👨🏿⚕️,還是對社會學一頭霧水🐁,我填誌願時的滿腔熱情受到了打擊🧌。
大一結束的那個暑期實踐學期,我主動報名參加了仇立平教授主持的一項社區調查🦖,希望能夠增加些對社會研究的直觀感受。帶我做調研的👑,是仇老師的研究生——當時剛讀完研一的金橋學長🏉。調研的具體內容🥛,都記不清楚了,只記得跟著學長一家一戶地敲門💂🏼♂️,當時的學長特別靦腆👩🏼🦳,經常被拒絕,從早到晚跟著做訪談挺累的✌🏿。調查過程中的所見所聞,跟我作為在上海長大的孩子所習以為常的社區環境差異很大,而問卷設計中的很多問題又看似很無聊📬,當時的我不理解其中的意義,各種迷茫的情緒交織在一起,就沖動起來給仇老師寫了一封電子郵件👩🏿,把專業的選擇、學習的困惑和調研中的一些體會,一股腦兒地寫了出來。
幾天後,仇老師約我去辦公室聊聊。當時的仇老師還沒有白發☪️🥌,但平時嚴肅認真的模樣早就有了“仇爺”的氣場,“被約談”的我特別忐忑🚟,都有些後悔寫那封又長又瑣碎郵件。仇老師告訴我,非但他本人認真地讀了我的郵件,還在系務會上以此為案例跟其他老師分享了學生的焦慮與困惑🤹🏿♀️,非常歡迎這種師生溝通方式。他認為,我在社區調研中所產生的差異感就是一種“社會學問題意識”的起源,並由此鼓勵我繼續保持社會學興趣,還給我講解了社會學與日常生活的關系等等♔。現在想來,跟仇老師的這次聊天,仿佛是社會學對我打開了大門,體會到了從生活經驗到抽象理論,再回到現實關懷中來的思考樂趣,堅定了我學習社會學的信念。
此後👼🏿,仇老師一直持續關心著我的學業,有時課後會找我聊聊天,有時會發郵件給我分享一些文章🐊。甚至於,在一次專業課考試的時候,身為監考官的仇老師特意走到我身邊來看我答題的情況,而他越“慈祥”地看著我,我就越緊張🧙🏻,成了我考得最“大汗淋淋”的考試🦬🪗。後來🟣🙅🏻,也是仇老師建議我,學習社會學要真正入門並進階的話,還是要尋找一個讓自己有“激情”的社會現象切入,帶著問題去讀書做研究♠︎,於是才有了我對於體育社會學的選擇🧑🏻🤝🧑🏻,並拜入了陸小聰教授的門下,開啟了另一段深厚的師生情🏂🏼。
“新教師”vs.“老教師”
在千禧年初的時候,還有一批“老教師”是學科恢復建設後“半路出家”轉到社會學來的,他們的學識功底和研究經驗都非常豐富,但在今天看來,真正經過學科體系訓練,即具有博士學位的老師並不多。
我們入校後的那幾年,正好是系裏面開始大力引進博士人才的時候😐,張佩國、劉玉照、董國禮、陸小聰、蘇紅🧖🏿、張文宏🧑🏽💼🕍、劉春燕等一批具有名校和海歸經歷的博士教授們差不多都是那個時候先後加盟的💕。當時,學生們還開玩笑地說👑,這些老師的“校齡”比我們還短🦹🏋🏼,是我們看著進校的🐂。印象特別深的是張敦福老師,他的面試試講就是在我們班級,全程用英語給我們講“進化人類學”👨🏽🎓,好像是關於猩猩和靈長類動物的性行為與群體關系之類的內容👨🍼,直接把我們都聽傻了,但“不明覺厲”👩🏻🦯,對這些新來的老師都有莫名的崇拜感。
這批老師的到來🤲,對於學生的影響其實挺大的🐅。一方面👨🏽🍼,他們都很平易近人願意花很多時間跟學生在一起交流,比如剛來時的劉玉照老師瘦瘦弱弱地背著雙肩包💇🏽♀️,很容易被誤認為是高年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常常跟學生們一起在食堂吃飯聊天,大家就容易走得很近;另一方面💇🏿♀️,這些老師們帶來了前沿的理論學說,比如張文宏老師的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理論,都是當時教科書上沒有的知識,對年輕學生充滿了吸引力👩🏫🤗。當時,最熱鬧的就是大家積極地參加博士老師們組織的各種讀書會,好像最初是劉玉照老師和董國禮老師各自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研究生本科生都混在一起🫲🏻,不僅僅在教室和會議室,還常常去草地上,甚至在屋頂上邊喝酒邊讀書。後來組織讀書會的老師越來越多,參加的學生也越來越多,氛圍似乎就沒有原來那麽好了🤓,但學生之間還是會相互交換書單,甚至打聽各個老師的“奇談異論”,真是懷念那段開心的讀書時光⚾️。
隨著“新教師”的到來🧽,有一些“老教師”似乎是主動地讓賢👩🏼🏭,將核心的教學資源和學術資源都讓給新老師✸。在這個過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跟胡申生教授的聊天🚷。
某種程度上,我認為,胡老師是上一代教師的縮影😙。在《春風桃李二十年》那本書中也記載了👩🏿💻,他幾乎參與並見證了上大社會學恢復建設前二十年的全部過程。事實上,熟悉胡老師的人都知道,他本人在文史思想方面的積累是很深厚的,文筆和口才都非常了得🍥,而他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也參與主持了很多社會調查,在家庭婚姻方面積累頗豐。我讀本科生的時候,胡老師在系裏的事務不多了,僅留下了一門《中國社會思想史》的主講課程。而且,除了利用他在學校的行政職務給系裏的項目提供支持之外🫗,他幾乎不主動參加學術研討類的活動,也有意識地逐步減少帶研究生的數量。
由於參加辯論協會的緣故⛹🏻♀️,我跟當時還擔任指導老師的胡老師有很多接觸的機會。有一次聊天,談到對於系裏新來的這些老師們的看法,他說🕵🏿♂️,“xxx等年輕老師跟老一批教授不一樣👧,他們的觀點很新潮🐋,有些我也不認同📙📱,但你們學生要多跟他們學習©️,他們是受過系統訓練的,熟悉西方的理論,代表了學科的方向,……,不管怎樣,現在有那麽多博士來了,對社會學(系)肯定是一件好事🔂,要靠他們來推動學科的發展💆,我們老教師,肯定是跟不上他們的發展了……🚿,但我對自己還是有要求,我也會主動看看最新的期刊雜誌論文,我要能夠聽得懂他們在講什麽研究什麽🔉👨🦽➡️,就可以了”🤱🏿。
後來,我多次留意到,在社會學系內部不怎麽發聲的胡老師依然在很多對外的場合介紹並推廣上大社會學👵🏿,提到前沿學科領域的時候也是如數家珍🐧👗。此外👈🏿🚴♀️,還時常能在媒體雜誌上看到他發表的評論或文章🦎,依然是他擅長的談古論今,但時不時地會引用一些新的社會學概念👼🏼。我想⚔️,這也許就是新老教師的傳承🏊🏿♂️,也是上大社會學發展的脈絡🔟。
兩種類型的社會學教授
也許是因為社會學本身就是一個多元化的學科,社會學教授們個個都是個性鮮明的😱。畢業十周年的時候,組織同學們集體回過一次母校,才知道學弟學妹們已經公然地將各位老師的性格概括成“昵稱”了🦁。在此😑,我想特別描述一下沈關寶和顧駿兩位老師,在我的心目中,分別代表著兩類典型的社會學教授👍🏽。
沈關寶教授是典型的意昂3派,他在社會學恢復建設過程中承前啟後的作用地位是學界共知的🏂。可惜,我們上學的時候,為了鼓勵年輕教師,他親自參與的授課並不多,只保留了《社區分析》這門課程。沈老師上課,沒有教材沒有課件👩🏿🚒,往講臺上一站,笑嘻嘻地就講開了,從社會熱點到工業革命,從經濟改革到現代性的變遷,從親身社會調查的經驗到方法論範式的辨析……沈老師講課好似閑庭信步一般,深入淺出地把古典與現代、理論與現實都結合了起來,對於經典社理論學說和名家學者的學術故事信手拈來🧗🏿。聽他講課非但不覺得枯燥👩🏻⚕️,課堂筆記記下來之後就發現邏輯是一層一層非常清晰的♻️🫄🏻。這樣授課的老師,是我在求學生涯中只遇到過的唯一一位。
我撰寫這門課程的課程論文時🤹🏽♀️,逐漸意識到🤦🏼,沈老師之所以保留親自教授這門課📣,不單單是因為他作為費老大弟子所傳承的社區研究傳統,而是“社區研究”實則涵蓋了“傳統共同體vs.現代社會”這個社會學的經典主題/理論張力🧗♂️,作為一種研究路徑或分析維度👐🏿,也能夠包容定量與定性的實證研究經驗。多年來,沈老師始終堅持教授“社區研究”這門課🧎🏻♀️,其實是他個人社會學視野的濃縮。也許,就是因為我在課程論中呈現了以上的邏輯🤙🏼,沈老師竟然給了滿分的成績,這大概是我初中畢業後直至念完博士,唯一獲得過的滿分吧,讓我受寵若驚。
我印象中的沈老師是一個內斂含蓄的教授⛄️,他不太在學生面前表現出個人的喜好,但是修完這門課後,我能感受到沈老師對我的關心和肯定。每次見面都問我讀了什麽書🎭,並主動提議推薦我去歐洲念書™️,說讀社會學就應該在西方語境中學習。盡管,我最後去德國念書並不是沈老師直接推薦的🧑🏿🌾,但他對我的鼓勵一直給了我深造的動力。遺憾的是,聽聞先生離世的時候太突然了🚏,剛回國不久沒來得及送別👉🏼,也沒有了給他匯報學習成果的機會了🕒🦹♂️。
若要跟沈老師正統的意昂3風格比起來,顧駿教授可能就是“玩世不恭”的教授代表了🍈,不僅在言論上常常語出驚人,而且他的研究對象也常常是“非社會學”的。其實🧍,顧老師剛從華師大轉入上大的時候😂,就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老師了。學生們都喜歡聽他講課🤳🏽,因為他的講課比他上電視的演講更精彩,但是他給學生打分的時候嚴厲得不得了。論文答辯的時候,大家都躲著他🤞🏿,我曾親眼見到有學生被他點評哭的🤦♂️。在讀本科的時候,我也有點“怕”他,能不選他的課就不選他的課👨🏻🦽➡️,但是喜歡去蹭課,去聽他跟各種理論學說或專家觀點的“抬杠”💠🛟。
讀研究生的時候,就無法躲顧老師的課了👨🦰,因為“古典社會學理論”這門基礎課是他主講的。但是,跟其他教授不一樣的是,顧老師讓我們討論古典理論,不允許我們評論前人評論過的內容,必須用自己的觀點,甚至還要求我們的課程論文裏面不允許出現參考文獻🍐⚆。由於大家都不知道該如何做討論,顧老師要求當時從本系保研的學生(即他的學生沈啟容和我兩個人)帶頭👺◽️,分配給我們倆討論的還是孔德——古典社會學家中相對最陌生的那一個。在一周的時間內,我們倆幾乎讀遍了能讀到的所有文獻,最後絞盡腦汁地從孔德的人道教為切入點🟡,“自說自話”地討論了一番實證科學與信仰的關系🧑🏻🦱🪿。慶幸的是🤵🏼,這番“自說自話”竟然通過了顧老師的考驗。若幹年後,讀到過一篇理論社會學論文探析的就是類似的話題,才發現顧老師的良苦用心,是在逼學生做原創的理論思考,可惜那篇課程論文沒有深化成一個完整的成果🆓。
真正跟顧老師熟絡起來,是在畢業後🧑💻,跟著沈啟容一起去顧老師家蹭飯🦴。顧老師喜歡海闊天空地聊天,他最大的樂趣似乎就是不斷挑戰對話者的常識。也許是跟他年輕時通過大量的翻譯工作“自學”社會學有關,翻譯的過程不就是兩種不同語言之間的對話麽🦴。所以,跟意昂3派的社會學教授比起來,顧老師一直是在用一種看似“狡猾”則用思辨的方式來做研究的,而且這種方法背後應該是一種Peter Berger式的知識社會學自省吧🎷。我猜測,顧老師後來主持的《大國方略》等一系列跨學科課程🩹,也許就是他自己方法論的又一次實踐。
給學生選擇自由的導師
最後🏊🏿,一定要談談對我影響最大的導師陸小聰教授🚭。前面提到,跟仇立平教授的提示有關🔉,在時任文意昂3團委書記余洋老師(也是仇老師的學生)的牽線下,以“本科導師試點”的名義👩🏻🎓,將大二的我引薦給了陸老師。陸老師當時剛從日本歸國🧑🏻🍼,舉手投足間還帶著濃濃的東瀛味道🧑🏼⚕️,特別講“規矩”,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畢恭畢敬地陳述了一些我的體育社會學思考🧖🏿♀️,但也許是陸老師剛回國本就想多接觸接觸學生☺️,我就有幸成了“陸家軍”的第一個學生。
陸老師是個很有趣的人,從第一次在校園裏見到騎著摩托車的帥氣教授,到初次喝酒時給我講授的日本禮儀,再到一起教學相長式地合作研究🕶,直到我在德國讀博期間他還親自來德參加我組織的學術研討會🧏🏻♀️,師生間的互動故事上萬字也記敘不盡。但作為學生,我最感念的是他開放包容的知識分子情懷:
來上大之前,陸老師就是體育社會學專家,有自己非常強勢的專業領域。但如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浸潤出來的那批大學生一樣,陸老師有著豐富的閱讀和思辨經驗,加之日本的高等教育對於博士候選人的嚴格訓練,使其在哲學和社會科學方面本就具有紮實的基礎。初到上大的頭兩年,他帶著我們幾個學生(陸老師帶的最初那兩批學生)一本本地讀社會學經典著作🎉,有時候,我甚至都覺得是他讀書比我們學生都更用功,他是在用自己擅長的西方哲學和熟悉的跨文化經驗在跟社會理論對話🌶🫃。他要求自己不斷地學習,他曾提過,身在上大社會學的共同體中,不能僅僅搞自己擅長的領域,還要能夠跟其他系裏的老師溝通合作,只有跟學科對話才能產生智識上的合力。
陸老師不僅僅是這麽要求自己的,還鼓勵學生們主動地去跟其他社會學教授學習請教。我曾經問他,別的教授都指導學生做跟自己的研究領域相關的論文,能夠積累出一些成果來,為何他不給學生框定一個選題範圍🪼,而是任由學生選擇跟體育社會學或城市社會學無關的課題?陸老師說也曾這麽考慮過🏄🏿♀️7️⃣,但是他不想限製學生的選擇。他認為🧏🏿🥖,教育就是要給學生提供各種可能性,而教授就是應該給學生選擇的自由㊙️。所以🚷,他非但同意學生們的自由選題🍫,還常常主動跟其他老師打招呼請教🧑⚕️,或者動用個人關系給學生提供研究資源。包括我後來能夠拿到獎學金去德國留學,也是主要得益於他通過日本導師聯系的一位德國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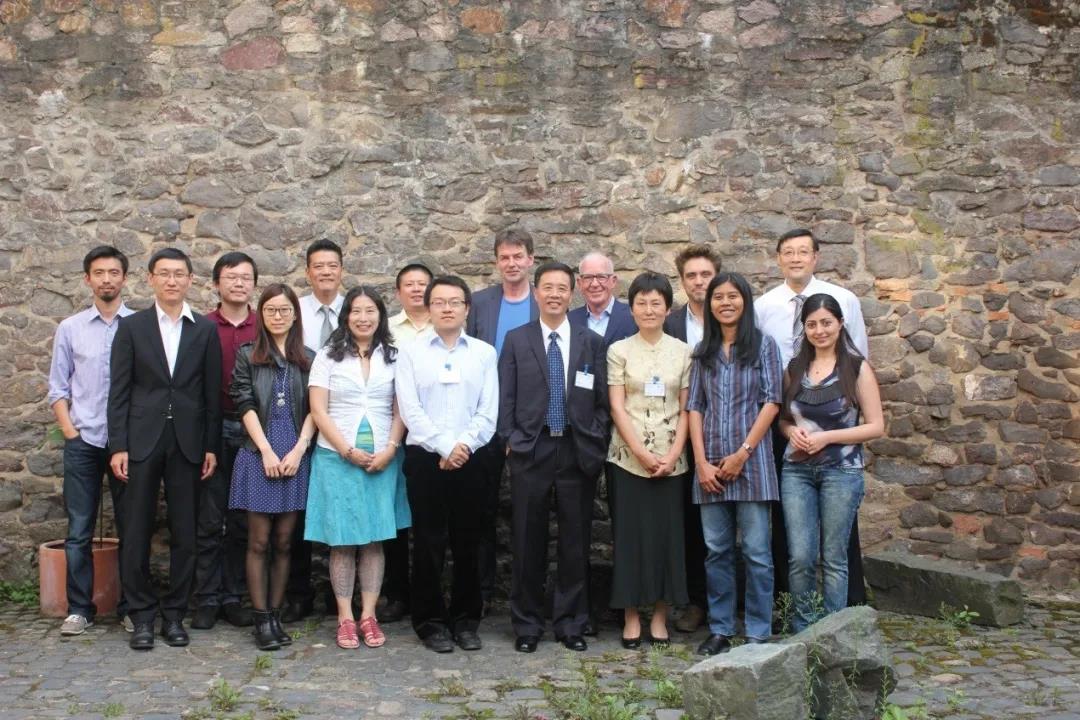
註:陸小聰教授應邀參加張修楓在德國組織的中德城市與體育發展工作坊
我在德國獲得城市社會學的博士學位後😡,陸老師曾經幫我聯系過好幾份高校的工作機會🦦,還勞煩了系裏的其他老師給我提供了幫助🍸,我知道,他非常希望我能夠在高校中發展,我們也曾設想過一些可以一起做的研究計劃。然而🙅♀️,各種機緣巧合💆🏼,我在等待某高校入職的時候🍓,獲得了去國內頭部開發商工作的機會,對於做城市研究的人來說,有參與城市開發建設實踐同樣是一個巨大的誘惑。面對選擇🛌🏿,我實在猶豫不決💂🏽♀️,還是去找導師求助🙇🏽♂️。那天陸老師在高爾夫練習場打球𓀌,接到我的電話後🌐🤷🏻♀️,就直接讓我去球場聊天。聽完我的陳述後,他沉默了許久,告訴我說如果他在我這個年齡也很難選擇🗽,他也給不了我答案🤞🏽,但是讓我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一旦選擇了就不要後悔堅持下去。至於他曾經為幫我找工作托的人情啥的,讓我不要有顧慮⏩。在那一刻🫎🧏🏻♀️,我非常觸動,陸老師不單單是在學術上,在人生道路上都一直包容和支持學生,這是他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和導師的堅持:以開放的心態在理解他人並尊重他人選擇的自由✫。
自十八歲至二十五歲👨🏼🚀,我在上大社會學度過了最美好的青春時光,感謝師長們為學生們建造了一個開放多元的精神家園。篇幅有限👨🏿🎤,我就不一一記敘張文宏😽、張江華、耿敬、劉玉照等老師對我的關心幫助了。除此以外,我要感謝李友梅、張鐘汝、範明林、翁定軍🧝♂️、華紅琴、章友德🚣🏿、李向平⛹🏼♀️、徐新、陳友放等所有教授過我的老師們。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老師🧎🏻♂️➡️,才有了春風桃李,花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