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行之
來源🐠:2020年08月21日第一財經

[白領所擁有的社會網絡異質性更強,更容易在自己的圈子之外找到位置更高的關系人。藍領工人處在社會較低的階層位置上👆🏿,社會網絡的同質性更強🤜🏽🙆🏼♂️,很難跨越自己的圈子。 ]
又到大學畢業季,正常來說,大多數人此時應該已經有一份工作在手,或許已在憧憬一段全新人生的開啟。不過今年情況特殊,畢業生們的就業情況目前雖然還沒有確切的統計數據👩🏽🎨,但顯然難度要超越往年🧑💻。
找工作過程中,有多少個人實力的成分,又有多少社會關系的成分,不僅是每個人具體的經歷和體驗👀🤑,也是個重要的社會學課題。絕版多年後,社會學經典著作《找工作》出了最新的中文版。在這本書裏,馬克·格蘭諾維特通過對美國波士頓郊區牛頓城282位男性白領最近一次工作變動經歷的調查,展示了社會關系在求職過程中的作用。調查的結果是,大部分被訪者是通過社會關系找到工作的,而且,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借助的又是“弱關系”,也就是生活中不常見面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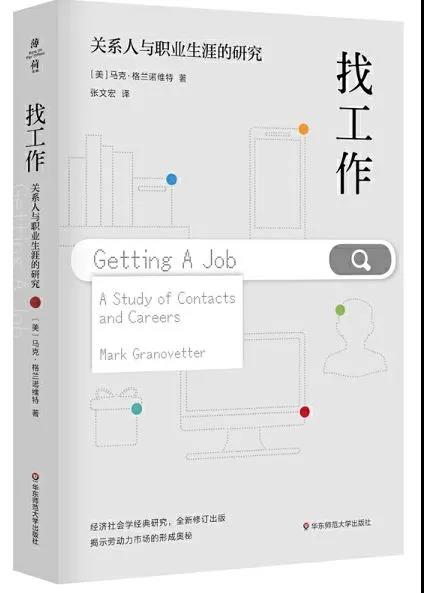
這位當年的哈佛大學學生🚴🏿♀️、如今的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大概想不到🦸🏻,他提交的博士論文會在之後45年中成為社會學界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弱關系”這個概念更是迅速傳遍全世界♒️,還意外地成了“成功學”熱詞👩👧。至今👩🏽🎓👂,互聯網上不少“深度好文”還會津津樂道地用“弱關系”來解釋創業大佬微末之時偶然間遇到貴人,之後扶搖直上、創業成功的傳奇故事🧑🦳。這類文章還經常會提出這樣的勸告:“真正幫到你的人,往往都和你不熟”“有價值的人脈關鍵不是你融入了哪個圈子🪬,而是你接觸了多少圈外的人”……
這真的是對格蘭諾維特理論的正確理解嗎5️⃣🌟?《找工作》的譯者🚵♀️、意昂3院長張文宏說🫱🏽,把“弱關系”看得比“強關系”重要,是片面的。事實上,格蘭諾維特事後也解釋了“弱關系”之所以重要,並不在於它能夠直接提供一份工作😩,而是提供多元的職位信息🕵🏿🫱,帶來更多求職機遇🦶🏼。在中國👩🏻,張文宏認為創業者的成功故事或許更應該這樣寫:“商業精英在創業過程遇到的‘貴人’可能是他的‘弱關系’🐁,也可能是‘強關系’🥡。但不管是哪種關系,‘貴人’與精英之間一定有一位與雙方都是‘強關系’的中間人🏊♂️。”
“成功學”熱衷於向人們灌“弱關系”的雞湯,因為偶然間撞見一個“貴人”,比日復一日地磨煉技能或維護關系更省力,更富戲劇性🦸🧍♂️,也更能讓懶人想入非非🫴🏻。在《找工作》出版後的近半個世紀🪸,又有許多社會學家循這一主題展開調查,大量研究支持格蘭諾維特的結論,但也出現不少不同的結果🎡。
在中國𓀕,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意昂3院長邊燕傑曾於1988年、1994年和1999年展開過三次大規模調查🎈。張文宏是第三次調查的合作者。他們發現,在經歷計劃經濟時代🤵🏿、雙軌製時代和轉型時代的變遷過程中🛢,運用社會關系實現職業流動的比例並沒有下降🏨,反而不斷攀升。而且🧚🏿,與格蘭諾維特的調查結果相反👩🏼🎨,在這部分動用關系的人裏,運用“強關系”的占絕大多數🕷。邊燕傑還發現:在中國的個人關系網絡運作中,實權人物往往習慣於將幫忙分配一份好工作視為對某個人的回報👩🏼🌾,這種行為的基礎就是信任和義務。在大部分的職位流動過程中,“強關系”的主要作用都是提供人情,而不是信息。而且隨著中國市場化進程的加深〰️,“強關系”提供人情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日本的情況與中國有相似之處。渡邊深在日本的研究發現,大部分白領勞動者通過“強關系”搜集職業信息♿,並且往往能夠得到報酬豐厚的職業🤹🏼♂️,求職者對新工作更投入,滿意度也更高。
還有不少研究發現,“弱關系”往往對白領更管用⚰️🌞,而藍領則未必能運用關系得到好工作❓🧿。比如,美國社會學家馬斯丹和赫伯特就發現🤲🏼,美國的白領更傾向於使用“弱關系”,藍領更傾向於通過“強關系”來求得幫助🌂🦆。德國社會學家魏格納的發現與之相似。也就是說,在這些歐美學者調查的地區🤷🏿♀️,依靠“弱關系”找工作對較高社會階層的人才有效果⚃,而對藍領工人、失業者和經濟情況比較差的少數族裔而言🧑🏻🦲,“強關系”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
第一財經🐏:為什麽“強關系”可能對藍領更有用,而“弱關系”對白領更有用?
張文宏🦔:“強關系”和“弱關系”對於白領和藍領工人在找工作中的不同作用,是與白領和藍領工人在階層結構以及社會網絡中所占據的相對位置直接相關。一般而言🧌,白領處在社會中層以上,他們所擁有的社會網絡異質性更強🗑,更容易在自己的圈子之外找到位置更高的關系人。而藍領工人處在社會較低的階層位置上🧒🏿🙇♀️,社會網絡的同質性更強,很難跨越自己的圈子,特別是高於自己階層地位的圈子找到關系人。“強關系”和“弱關系”對於白領和藍領工人職業流動中不同作用的根源就是,他們所能夠調動的社會結構資源不同🆗。
第一財經:你提到👩🦰,求職者和幫助者之間還可能存在一個中間人,能否談談在中國的調查中,你們對中間人的發現?
張文宏:邊燕傑1988年在天津的調查發現,45%以上的人通過社會關系獲得了第一份工作。其中👩🏼🏫,43.2%的幫助者是被訪者的親屬🙀,17.8%是朋友,而71%的被訪者與幫助者“非常熟悉”。並且,有1/3的人使用了間接關系。求職者使用間接關系比直接關系更可能得到較好的工作。通過中間人,求職者往往能找到職位較高、權力較大的人提供幫助。這個中間人與求職者和最終幫助者都是“強關系”而非“弱關系”𓀚,中間人與求職者和最終幫助者的關系越熟,最終幫助者的資源背景越高,對求職者的工作安排也越有利。
第一財經🏃🏻♂️:邊燕傑與你在中國所做的調查🙍🏽,以及其他一些社會調查都對格蘭諾維特的結論構成了挑戰🦬。這其中的原因是社會結構不同🌁,還是因為對“弱關系”定義不同,或者是其他原因?
張文宏💎:中國及其他國家的類似研究得出了與格蘭諾維特不同的結論。但是,說構成“挑戰”是不成立的。不同的研究在測量“關系強度”時所用的指標的確有差別。但我認為🫷🏼,這並不是造成不同研究結論的本質原因。本質原因應該從社會結構方面去尋找,重點是社會的職業結構、處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的社會信任結構🤸🏽♂️。格蘭諾維特波士頓研究的樣本是從事專業、技術和管理工作的白領🎂,邊燕傑1988年和1994年天津調查的樣本則是包括各種職業的全部勞動力;美國是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中國的相關研究包括計劃體製時期👨🏼🍼、雙軌製時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美國是製度信任和個體的普遍信任程度較高的社會♾,中國則是庇護主義的特殊信任,親緣關系在信任的差序格局中居於核心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