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馬丹丹👨🏻🦳👩🏼🔧,發表於2022年10月26日的《中國社會科學報》07版社會學,中國社會科學網
人類學家向往田野,因為田野不僅是學術發現之旅的起始🤸🏽,還是留刻自己足跡的所在🤸♂️。就此而言,不斷返回田野就是不斷回到起始之地,不斷刻烙自己的痕跡。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重返田野是人類學家的本性使然🕵🏻♂️,是學術激情的自然流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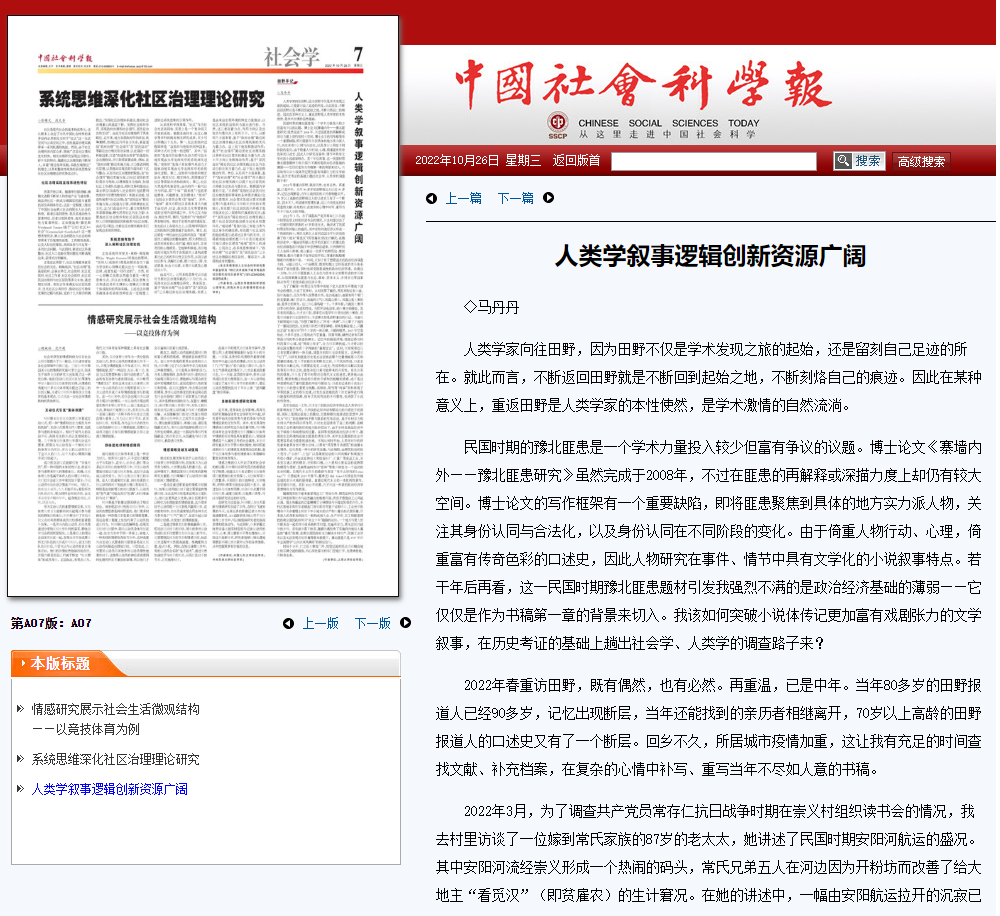
民國時期的豫北匪患是一個學術力量投入較少但富有爭議的議題。博士論文《寨墻內外——豫北匪患研究》雖然完成於2008年,不過在匪患的再解釋或深描力度上卻仍有較大空間➝。博士論文的寫作框架有一個重要缺陷,即將匪患聚焦到具體的地方實力派人物,關註其身份認同與合法化🧘🏼,以及身份認同在不同階段的變化。由於倚重人物行動💌、心理,倚重富有傳奇色彩的口述史,因此人物研究在事件👨🏻🦱、情節中具有文學化的小說敘事特點。若幹年後再看🗓,這一民國時期豫北匪患題材引發我強烈不滿的是政治經濟基礎的薄弱——它僅僅是作為書稿第一章的背景來切入。我該如何突破小說體傳記更加富有戲劇張力的文學敘事,在歷史考證的基礎上趟出社會學、人類學的調查路子來🚹?
2022年春重訪田野👨🏿🍳,既有偶然,也有必然⁉️。再重溫,已是中年。當年80多歲的田野報道人已經90多歲,記憶出現斷層,當年還能找到的親歷者相繼離開,70歲以上高齡的田野報道人的口述史又有了一個斷層。回鄉不久,所居城市疫情加重,這讓我有充足的時間查找文獻🤦♀️、補充檔案,在復雜的心情中補寫、重寫當年不盡如人意的書稿。
2022年3月,為了調查共產黨員常存仁抗日戰爭時期在崇義村組織讀書會的情況💆🏼♂️,我去村裏訪談了一位嫁到常氏家族的87歲的老太太,她講述了民國時期安陽河航運的盛況🧎。其中安陽河流經崇義形成一個熱鬧的碼頭📿,常氏兄弟五人在河邊因為開粉坊而改善了給大地主“看覓漢”(即貧雇農)的生計窘況。在她的講述中❤️🔥,一幅由安陽航運拉開的沉寂已久的豫北政治經濟畫卷在我的腦子中忽然鮮活起來🎩,我仿佛聽到工人在碼頭卸載🛻🪃、裝運重達一百多斤的棉花包🫴、煤炭和糧食💆♀️,船夫弓著身子在岸邊拉纖而讓笨重的航船緩緩前行的嘈雜聲音🩰🤱🏼。一瞬間,我似乎有了想要追求的政治經濟調查方向。從航運切入🧑🏻🦯,一個由棉花、煤炭和煙土交織而成的市場體系構成了滋生匪患,同時也深受匪患滋擾的政治經濟環境。沿著這一方向,我試圖將匪患嵌入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發展形成的市場體系,從而探索豫北匪患與生態、革命、資本主義📞🦟、鄉村暴力等因素綜合作用下的復雜政治經濟條件。
為了了解同一時期王漢華等中共地下黨人在家鄉開展地下讀書會的情況,我去了瓦亭村。從村民那了解到,西瓦亭附近有大廟,俗稱高廟臺,王漢華等人在那裏教書。走訪高廟臺,廟裏有兩個看門的老婆婆👨🏼🎤,她們告訴我,高廟的名氣比鳳凰山都大🐱。鳳凰山是大寒的廟,是李臺的家鄉👩🏻🦯。這讓我心裏咯噔一下。十多年前🧓🏿,我跑到大寒尋訪李臺的身世、事跡和傳說🫱🏽。當即開動電動車🎶,向大寒方向駛去✧。及至來到鳳凰山,我才意識到,原來它就是早年我尋訪過的大寒宮🚚👩🏻💼。但是我對廟宇絲毫沒有印象,不過碑文卻是田野重訪的標記。當廟祝不耐煩地對我說,“你想了解李臺🧜🏿♂️🤹🏻♀️,門外有一塊碑”🕍,我還暈乎乎地找了一圈說沒找到,無奈他只好把我帶到碑前。原來是躺在地上、只露出正面“鄉閭保障”四個大字的一塊石碑🏊🏿。我頓時啞然🧙🏽♂️。2007年它是如此🧑🎤,十多年過去,還是如此與它重逢。回看書稿,赫然記錄有石碑背面刻寫的李臺事跡的碑文。記憶中的畫面浮現🪿:恍惚記得當時村民看我心誠,說“背面還有字”👇🏻,合力將石碑扶起,我才得以抄錄這段完整的有若幹字殘缺的“蓋棺定論”。這時,我發現旁邊還立有安置石碑的一塊石礎,調查當初卻絲毫沒有留意。這種感覺“對了”,我研究的匪患歷史是無論安放在哪個位置都略顯突兀和困窘的境地,它介於官修歷史和野史之間🥖,介於民間傳說、口述史和檔案文獻之間🏄🏼♀️🎍,我需要在黨史🏢✴️、口述史🧑🏼⚕️、傳說和檔案文獻以及建築等實物考古之間,修復雜亂線索可能帶來的真實性。有關真實性的修復,我失去了青年時期對後現代主義的迷戀,更多地從由棉花、煤炭和煙土構成的物質世界感知到粗糙的質感🔎,或許是這種質感構成了重寫匪患的沖動與驅動力🫡。口述史記錄的小農生計貧窮比我的想象要更為殘酷,而報紙、期刊等“時事”資料再現了早期民族工業的艱難處境🤦♀️,對發生在老城的若幹歷史事件進行現場勘查和刑偵探測,彌補了民間傳說的不可靠性,也消弭了小說的傳奇性。
及至完成這一工作,我才意識到政治經濟學和生態人類學對我的影響發生了作用,我所說的近似沖動和驅動力的物質世界的質感💁🏿🏌🏽♂️,實際上是理論層面上的震動,它潛移默化地滲透到思想中🩱,轉化為“可見”的處理材料矛盾與聯系的寫作活動。基於鄉村暴力和鄉村破產的協同破壞作用,我對生態因素有了自己的判斷🤚🏻:在畸形的工業環境和放任的地方政府管治下,由於鄉村在商品經濟中處於被掠奪和被侵蝕的位置,在同等貧困的政治經濟條件下,脆弱的生態環境構成滋生匪患的誘發條件👨🏿🚀👨🏻🎨,其中生態脆弱的農業聚落更容易成為匪患的滋生地💭。不知從何時開始🐁,人類學對物的研究愈來愈具有世界想象意味,還帶有“風花雪月詩酒花”的浪漫主義情懷。這當然是一種物的研究旨趣,與此相較✡️,由棉花拉動的裕大花行、廣益紗廠👩🏽🦰、打包廠以及煤炭拉動的六河溝煤礦和周圍分布的小煤礦,並由此延伸出大和恒面粉廠、打蛋廠等食品工業🙋♀️🎙,關系到普通人家的棉衣、燃料和口糧🚴🏿♀️,讓大麥和小麥各自的成熟期和棉花與菜籽、芝麻等油料作物“套種”等常識轉變為一個迫切的生存問題。後現代主義聚焦的修辭與表征“有什麽好玩的(what fun)”👃🏼?我想起來2019年春節,葛希芝(Hill Gates)教授在加州她自建的農場木閣的廚房裏🧑🏽🚀,拿著後現代主義的一本批判性著作🦸🏽👩🏫,堅定地對我說。直到2022年初夏,我才將這一樸素的政治經濟學思想轉化為寫作源泉。
隨著現實世界愈來愈顯現出工廠勞動條件🐍👬🏼、棉花品種良劣和礦井工種差別等技術與自然融合的粗糲界面,勞資矛盾推動工運風起雲湧,煙土和毒品的泛濫模糊了士紳群體與不穩定階級的界限🦹🏿,鄉村武裝地主和聚集老城高門深宅的貴胄富戶遙相呼應,工業世界的嘈雜聲夾雜著煙土刺激下中小地主的破產和大毒梟的武裝販毒,日本浪人的身影如同幽靈一般構成被失業、生產停滯🛒、罷工和匪患侵擾的南京國民政府所謂“黃金十年”隱隱的威脅。一個地方與更大世界聯系在一起的市場體系既積累財富☘️,也遍布暴力,更無法阻擋戰爭的步伐🟪。直奉戰爭落下帷幕,隨著偽滿加快了實施向內地輸入毒品的“毒化”政策,在南京國民政府無力解決鄉村破產🦎、民族工業債務以及無法實現徹底禁毒等根本前提下,豫北匪患只是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飄搖信號。
時隔十余年🟢,佇立在大寒宮門外,恍惚記起村民合力將躺在地上的石碑立起的畫面,內心深處緊閉的柴門忽地打開🕎🐳,鬼使神差地,我轉身走來。


